工業互聯網或工業物聯網在美國和歐洲已基本不作區分地使用,通指互聯網的核心技術,也就是計算和通訊網絡技術,在工業系統中更加廣泛、更加深入的應用,也就是對工業系統的全面信息化。
我個人比較喜歡工業互聯網這個詞,它的涵蓋面更為廣泛些,包括從實體(也就是傳感、執行和控制器件、產品和裝備等等)、信息系統、業務流程和人員,不至于過分強調實體物件。雖然對實物的連接在目前很重要,但在若干年后,實物也會變成系統中正常的一部分,其特殊性會降低。

美國制造業創新中心的發展
在美國,奧巴馬總統在其第一任期內就開始了一系列的政策舉措,以振興美國制造業。最顯著的成果是在其第二任期內啟動的美國制造業創新中心(Manufacturing USA)一個通過公共機構與私營企業合作伙伴(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機制,建立了一系列的制造創新研究院(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Institute),構成一張網絡,分布于全國各地。
政府為每個研究院提供總數為5千萬到1.1億美元之間的資金,周期為5年;其它50%以上的資金則由企業和其它非政府來源提供。這些創新研究院通過建立一個聚合企業、政府和學術界資源的創新生態環境,融合人、意念和技術,旨在孵化新興產業的創新、促進技術轉型、支持具有應用前景的產品和服務的早期研發,推動新產品早日進入市場;在此同時,并著力培訓制造業勞動力和技術人才。
每個創新研究院有專門而具體的課題,聚焦在一些具有潛力的關鍵制造業技術,綜合起來,涵蓋面相當廣,目前包括了先進材料(新型纖維和紡織、復合、輕型、先進碳化硅和氮化鎵半導體材料)、先進工藝和技術(集成光子器件、添加性制造、寬帶隙(WBG)半導體電力器件、柔性混成電路板、生物制藥、細胞組織生物制造、模塊化的化學過程強化工程)、先進裝備(先進機器人)、節能減耗技術(凈能制造、降低體現能源和碳排放量)和信息化制造。而狹義的智能制造——也就是制造業的信息化,在現有的14個研究院中只占了1.5個(信息化制造和能耗優化)。
由于市場經濟的觀念在美國根深蒂固,政府在技術和商業方面的影響力相當有限,(除了通過稅務法規調節之外)難以對其有直接和實際的干預。如美國制造業創新中心在其2016年的年度報告中所指出,其工作重點在于縮短技術發明從大學和科研機構到工廠車間的距離。聯邦政府的角色僅限于在美國制造業所面臨的關鍵機遇上,創建以企業為主導的應用研究合作空間。
這些創新研究院的成果,對推動美國的制造業的發展預期會有一定的貢獻,但這些項目的運作周期為5-7年,其影響力將在在若干年后才能有效地評估。在總體上可以預測,美國在工業互聯網和智能制造方面,將一如既往,由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特別是新創企業,通過對新技術和新的商業模式的不斷探索和實踐來推進、靠企業自身業務價值的實現和市場競爭的驅動而實現。
制造業企業的信息化過程
對于制造業企業的信息化過程,簡單而言,完善對各個業務和生產環節的信息化是第一步,如在以EPR為主線的價值鏈各個環節,還有對以PLM為主的產品鏈各個環節部署和使用相應的工業軟件,還有在這兩條鏈的交叉點上的生產環境里實施MES,這些都是基礎。
第二步是要將這些環節的信息化模塊(專門工業軟件)互聯互通,在價值鏈和產品鏈上逐步實現流程的自動化,并使能對生產各個環節數據的收集。
在此同時,作為第三步,對設備進行連接,收集設備運營和產品在生產過程中的數據,通過數據分析,優化生產過程。第四步,在對產品、設備以及生產和業務流程中收集了足夠的數據后,可以進行不同周期和跨越生產和業務環節的綜合性的大數據分析,識別和消除效率和績效瓶頸,對整個生產和業務過程進行宏觀性的優化。
最后第五步,打通在生態圈內企業之間的信息系統的互聯,實現企業之間的業務和生產的協同,把優化的范疇擴展到生態圈,以及對客戶部署了的產品實行連接,通過對產品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實現服務延伸,為企業的業務轉型開拓機遇。
這些步驟可作為制造業企業信息化的總體路線的一個基本參考,但沒有必要按部就班地實施。在起步時應該首先根據每家企業獨特的核心價值的訴求,制定企業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戰略愿景。在具體的實施中,以戰略愿景為指導,以業務價值為驅動,以先進技術為手段,以當務之急要解決的業務問題為突破口,通過一個從小到大,從簡單到復雜的迭代發展進程來實現價值和戰略愿景。
美國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的策略
美國的企業對于產業的數字化日益重視,特別是當華爾街的分析家已經開始向上市公司的CEO詢問企業的工業互聯網或數字化策略之后。美國的企業在信息化的程度也是參差不齊,國防、航天及大型高價值裝備制造商的信息化比較完善,高流量產品如汽車和其零配件的廠商的信息化也會相對完善,但其它的企業,特別是一些低流量的工程產品的廠商的信息化也還在發展過程中。一些在信息化起步早的企業面臨著一些很不一樣的挑戰,像如何規范化企業內部五花八門同類型但出于不同供應商的工業軟件,或如何更新部署了多年但現在還在大型機上運行的老舊工業軟件。
不同的企業在其數字化的策略也很不同。有像GE和卡特彼勒這些企業,他們把深厚的工業知識與數字化結合起來,充分利用新型裝備的數字化和連接性,在為客戶提供設備的維護方面切入,推動商業模式的轉型,從銷售設備,到銷售服務,最終到銷售成效,在這些過程中不斷地增加軟件在其產品總體價值結構的比例,也就是愈來愈多地利用軟件創造價值。一些這樣的企業,如GE,更進一步把他們的這種能力和經驗,通過工業互聯網平臺的方式,提供給其它的產業客戶,從而成為工業軟件服務平臺的提供商。
而其它更多的企業,在不動聲色地增強和完善企業內部的信息化,優化業務流程,提高設備的使用效益和降低成本(如在開始實施預測性維護)的同時,十分注重如何利用產品的連接性,收集數據,為客戶提供更多和更好的服務,為客戶創造更高的價值,從而也為企業開拓新的營業收入。
最近有些調查報告表明,絕大部分都美國制造業企業高度重視并大力推進工業互聯網技術對生產資源和流程進行數字化的改造而從中實現優化。
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企業已經部署了一定的工業互聯網解決方案,而且他們之中的98%表示這些部署對企業是重要或很重要的。而那些還沒有部署的,超過85%有計劃在一年內開始部署。
在另一方面,作為工業互聯網開創者的GE近期在市場表現不佳,引起了一些行內人士的關注,擔心是否是工業互聯網的一個挫折。我個人的看法是,工業互聯網的基本理念、方向和路徑是符合技術發展的趨勢的和業務價值的需求的。
GE的市場表現在我看來,主要是與業務經營和市場的消長有關,前些年GE對其結構的改造,旨在成為一家更純粹的工業企業,把注意力放在具有高增長潛力的包括數字化在內的產業,作了不少的投資,但這些投資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產生的相應的效益,不可能馬上提供的足夠經濟回報。工業互聯網或產業數字化剛起步,其進程所需要的時間會很長。
國內外架構的異同與側重點
目前在國際上有美國工業互聯網參考架構IIRA、德國工業4.0參考架構模型RAMI4.0、和日本工業價值鏈計劃IVI等。國內也有工業互聯網產業聯盟的《工業互聯網體系架構(版本1.0)》。
這幾個工業信息化的參考架構,盡管它們的出發點、思考問題的角度和所關注的應用領域各有差異,但它們都是共享著對產業實現全面的信息化的核心理念和技術基礎。
IIRA注重跨行業的通用性和互操作性,提供一套方法論和模型,以業務價值推動系統的設計,把數據分析作為核心,驅動工業聯網系統從設備到業務信息系統的端到端的全面優化。
RAMI4.0則深度聚焦于制造過程和價值鏈的生命周期,為其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三維模型。這個模型在對在制造環境里不同環節單元的功能的分析、它們之間的互操作性的需求的辨認,以及對相應的標準制定和采用,都十分有價值。
更值得關注的是與其相關的工業4.0部件模型,對包括數字化的零部件、設備、產線、車間、工廠、甚至信息化系統在內的所有資產提供一個統一的CPS模型,描述其功能、性能和狀態,并為它們之間的交互,從通訊協議、句法和語義,提供統一的界面。其廣泛實施,對推動制造環境各個系統的全面互聯互通,將會起著非常大的作用。
最近發布的IVI,從制造業一直追求的質量、成本和效率(產出)傳統要素加上環保要求的管理角度出發,結合生產環境的資產(人、流程、產品和工廠)角度和作業流程(計劃、執行、查驗和反應)角度,細分出智能制造單元,對信息化在生產過程的優化,作了細致的分析,進而提出了智能制造的總體功能模塊架構,在不同的(設備、車間、部門和企業)層次上,分析知識/工程流程(相當于產品鏈)和供給流程(相當于價值鏈)的各個環節的具體功能構成,頗具有獨到之處。
中國的工業互聯網產業聯盟年初發布的《工業互聯網體系架構(版本1.0)》把網絡、數據和安全作為工業互聯網體系架構的三大核心體系,對其現狀和發展趨勢,特別是針對制造業,進行了深度剖析,并提出實施建議。
這個體系架構對工業互聯網支撐的應用也作了分類和分析,從產業到互聯網的視角,歸納為四大類,包括企業內的智能化生產、企業間的網絡化協同、企業與用戶間的個性化定制、和企業與產品間的服務化延伸。這些對工業互聯網的發展都具有指導性的作用。
最近美國工業互聯網同盟與德國工業4.0的機構共同發布了一份關于IIRA與RAMI4.0對接分析的白皮書,指出IIRA與RAMI4.0在概念、方法和模型等方面有不少相互對應和相似之處,而差異之處則互補性很強,相互之間可以取長補短。
這個結論在對降低由于多個架構的存在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有一定的良好作用。相信這個結論,在這幾個架構之間都是適用的。所以,在這個方面加強國際合作,對國內和國際上工業互聯網和智能制造的發展都是會有益的。


 手機資訊
手機資訊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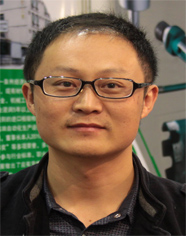


 豫公網安備41019702003646號
豫公網安備4101970200364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