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是深受高耗能、環境污染等困擾的電解鋁企業,一方是長期渴望經濟發展且擁有富庶資源的西部地方政府,當二者碰到一起之時,一場電解鋁西進運動就開始了。”這是筆者在媒體上看到的一篇報道。近幾年,隨著能源、人力等要素成本的增加,眾多的產業不堪重負,開始向能源富足的西部轉移,尋求突破瓶頸制約,特別是有色金屬中的鋁產業轉移態勢尤盛。
有色金屬產業“西遷”成為行業內外熱切關注的話題,西部已成為有色投資的“熱土”,這種趨勢是符合結構調整要求的。但是,讓人憂慮的是西部蓬勃興起的有色產業轉移是以大量消耗資源和粗放經營為特征的,屬于“高資本投入、高資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發展模式。中西部地區水資源匱乏,生態環境脆弱,高耗能產業的過快發展帶來的“高污染”,勢必將會使西部脆弱的生態環境雪上加霜。
要改善這一被動局面,一方面,產業轉移要將先進技術與西部資源深度結合,不能將傳統的高耗能、高污染項目“搬”到西部。嚴格執行產業政策和準入條件,通過規劃等手段對發展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類型、規模、布局進行調整,以最小的資源環境成本實現經濟增長,以最小的經濟成本進行污染治理。要把產業對接和調結構、轉方式結合起來,充分發揮西部的資源優勢和政策優勢,把新技術、新工藝用到西部,通過技術裝備的現代化,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延長產業鏈,提高產品附加值和資源利用率,在西部探索一條有色金屬工業發展的新路。嚴格控制鋁冶煉產能作為首要任務,限制無序擴張。
另一方面,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污染治理在保護環境方面只是“治標之策”,而在其大發展迅速積累資金后進行產業結構升級或者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才是“治本之道”。
這種策略已經在內蒙古準格爾旗有所體現。準格爾旗是資源富集的地方,卻不是在國家生態安全和生物多樣性中有重要地位的地方。這種地方,環境遭到破壞,一是損失比較小,且幾乎不存在不可逆轉的環境變化;二是恢復代價比較低。所以應該先發展,后治理。準格爾旗的發展思路總結起來就是四句話:迅速打好經濟基礎、優先改善人居環境、準備完成產業結構調整、慢慢進行環境治理。這樣,既有了經濟效益,也有了環境效益,這樣的發展模式值得西部其他地區借鑒。


 手機資訊
手機資訊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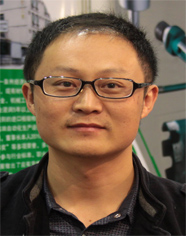



 豫公網安備41019702003646號
豫公網安備41019702003646號